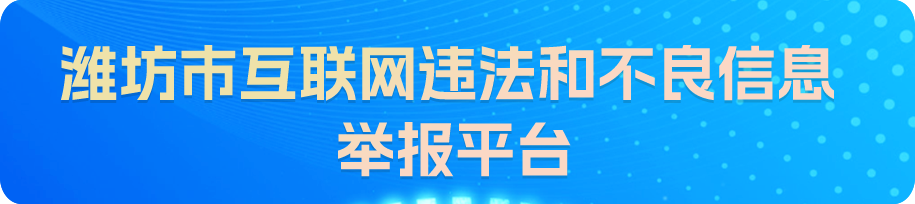为候鸟写诗
□孔祥秋
在我们所处的这个纬度,风和候鸟的走向大致相同。时令至此,风带来的是落叶,候鸟带来的也是落叶。
曾经,有朋友说我是候鸟的属性。我淡淡一笑,啥也没说,心里却很抵触。
的确,那时候,一村、一城、北山、南水,放肆颠沛,但不过是一时的年少疏狂,我对家是有很强的依赖性的。十几岁时,我倚着老枣树,读海子的诗:“从明天起,做一个幸福的人/喂马、劈柴,周游世界/从明天起,关心粮食和蔬菜……”
周游世界最终的归宿,还是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,归于那春暖花开的房子。
我有一间小房子,朝阳,在这里,我给候鸟写下两句话:“寒来南飞/暖来北行/不过是为了将高枝寻登。”
那时候,我对候鸟是不屑的,觉得这是一个贬义词。
父亲曾远走西北,在城里的日子倒也风生水起,可他还是毅然决然地回到了老家,耕田、放牛、编筐、挖沟,和季节环环相扣。父亲爱酒,暗暗的煤油灯光里,和邻家大叔高声地行着酒令:“螃蟹呀爪八个,两头尖尖这么大的个……该你喝你就喝,爷们喝酒别啰嗦……”
一个把弄钢铁的汉子,手把着夯把,成了村里将打夯歌唱得最响亮的那个人。
同一姓氏的村庄,街街相通,巷巷相连,家家相熟,人人相亲,从城市回来的父亲,一天天开心得不得了。作为父亲唯一生在老家的儿子,我渴望和他一样,守着这老屋,守着这一方农田。
对于“以梦为马”,我是这样理解的:可以凭梦策马狂奔,但最终还是守心于家园,所以我一边写诗,一边耩地、薅草、脱土坯。认识她,其实是在诗歌里,她在诗歌之外的意思是希望我去她的小城生活。我没有回答,只写下了几句话:“我不是候鸟/是和村庄的炊烟相依的风筝/离开了乡情的纤绳/那将何去何从?”
这诗,登在她小城的报上,她打来电话:“来接我!”
女儿的出生,让我无比欢喜。我觉得握住她的小手,就如同握着新鲜棉朵一样,会让人忘了疲惫和手上的老茧,忘了歉收的麦子以及烈日下干枯的玉米苗。女儿成了我苦心经营庄稼和篱笆墙最柔软、最温暖的理由。我,又想到了候鸟:“候鸟的构想/总是那么草率/因为不想付出全部的爱/春风里戏弄着邻岸的水/秋雨里又依偎深山的松。”
可是,我还是离开了老家。
离开老家的缘由是女儿病了,我和妻手足无措,只好来到她的小城。小城,离妻的父母近些,老人可以帮着照看孩子。
这城,妻子舒心,孩子快乐,只有我,望乡盼归。我,成了一只候鸟。老家无人看管,院子残破,空屋颓败,心好疼。
一个男人,不能谋山河,那就一定要谋家园,不能以自己的悲喜而随心所欲。从青春到白发,我把乡愁写成文字,却心无旁骛地守着这一城。守着守着,心底就有了一种痒痒的萌动,我知道那是新的根须在探寻、在伸展。
前天,我一个人坐在胶莱河边,看无数的候鸟起舞,我就想,它们飞越千万里,历经生死,是为了什么?
风起是生,风止是死,候鸟也是这个样子,原来,它们的生命就是征途,与荣辱无关,与富贵无关。忽然,我觉得一个人若是认知了风,那是在流浪;如果理解了风,那是曾经流浪过。流浪可以是一个大主题,也可以是一个小思维,比如在村子走向田野,在都市走向公园。人,一生都在行走。这,也可以说是流浪,是大大小小的征途。
或许都以为我没有誓言,寒来暑往都是新欢;或许都认为我没有诺言,万水千山都是背叛。其实,辜负了一双翅膀,才是懦弱,才是无可饶恕的背叛和谎言……
我,又为候鸟写了诗,我就这样一直为候鸟写诗。想一想,每个人一辈子都在写着候鸟的诗,长一首,短一首,各有不同而已。
编辑:冯淑杰
一审:冯淑杰 二审:李丽雪 三审:李中伟